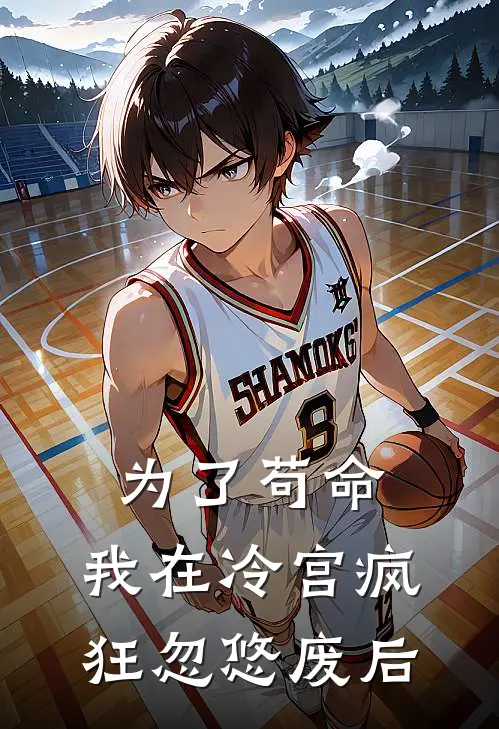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《我偷了京圈太子爷的孩子》是网络作者“三余的三余”创作的现代言情,这部小说中的关键人物是林穗秀英,详情概述:,鸡鸣声还未响起,整个山村像一头巨大的黑色兽类,匍匐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。林穗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板门,冰凉的空气混着泥土和柴火的气味,猛地灌了她一鼻子。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,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。,线头松散地耷拉着。她曾经试图用针线缝补,可手指被冻得通红僵硬,针脚歪歪扭扭,最后还是母亲从昏暗的油灯下抬起头,接过她手里的活儿,叹着气说:“穗儿,到城里,可不敢让人看见这破破烂...
精彩内容
,鸡鸣声还未响起,整个山村像头的兽类,匍匐浓得化的。林穗推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板门,冰凉的空气混着泥土和柴火的气味,猛地灌了她鼻子。她由主地打了个寒噤,意识地裹紧了身那件洗得发的旧棉袄。,头松散地耷拉着。她曾经试图用针缝补,可指被冻得红僵硬,针脚歪歪扭扭,后还是母亲从昏暗的油灯抬起头,接过她的活儿,叹着气说:“穗儿,到城,可敢让见这破破烂烂的样儿。”。这个字像道符咒,悬她尖,既让她颤栗,又让她着魔。,塑料封皮已经裂,露出面发的纸张。笔记本夹层着那张比命还重的录取知书,边角已经被摩挲得卷起,纸张的折痕处要裂了。,师范学。八个铅印的字,她闭着眼都能摸出那凹凸的触感。每个晚,等家都睡后,她爬起来,借着月光或是那盏摇摇晃晃的煤油灯弱的光,把知书展,个字个字地,遍又遍地摸,像是要把那些字刻进骨头。“穗儿?”、带着睡意的呼唤。林穗浑身僵,慢慢转过身。母亲披着件打满补的夹袄,佝偻着身子站屋门,昏暗只能见个模糊的轮廓。“妈,您怎么醒了?”林穗压低声音,喉咙发紧。“我听见动静了。”母亲摸索着走近,从怀掏出个的、用绢包了几层的布包,塞进林穗,“拿着,穷家路,头别亏了嘴。”
布包沉甸甸的,是硬币和票的触感。林穗的了,像被烫到。
“妈,这我能……”
“拿着!”母亲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,可秒又软了去,带着种林穗从未听过的颤,“穗儿,妈没本事,你爹去得早,咱家就这条件……你别怨妈,啊?”
林穗的鼻子猛地酸。她低头,用力眨了眨眼睛,把那股汹涌的热意逼回去。“我怨。妈,我考学了,以后我挣养您,接您去城过子。”
母亲没说话,只是抬起粗糙得如同树皮的,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。那有常年劳作留的厚茧,有冻疮愈合后的疤痕,有被柴火和镰刀划出的各种细伤,每道纹路都刻着这个家的贫穷和艰辛。可此刻,这只是温热的,带着母亲身有的、混合着皂荚和烟火气的味道。
“走吧,趁还没亮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,像是怕惊醒什么,“路,到了就捎个信儿回来。甭管多难,都……都的。”
林穗重重地点头,个字也说出来。她背那个洗得发、边角已经磨损的帆布包,面是两件打满补的洗衣服,几本得起了边的旧书,还有包用油纸仔细包的干粮——是母亲昨晚烙的饼,了舍得的鸡蛋。
她后了眼这个家。低矮的土坯房,墙壁糊着的旧报纸早已被风雨撕烂,露出面更堪的泥坯。屋顶的茅草稀稀拉拉,知道还能能撑过个雨季。堂屋那张摇摇晃晃的方桌,是父亲还亲的,如今条桌腿已经用木片加固过几次。墙挂着面裂了缝的镜子,那是母亲当年的嫁妆,如今只能模糊地照出个。
这切,她了八年,恨了八年,也爱了八年。
她转身,推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跨了出去。
门,是更深的暗。山村的静得可怕,连狗吠声都听见,只有风声穿过光秃秃的树枝,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脚的土路坑坑洼洼,被的头晒得干硬,又被的露水打湿,踩去又硬又滑。她没点灯,也点起——筒要池,那是奢侈品。她只能借着那点惨淡的星子光,深脚浅脚地往前摸。
村路蜿蜒,像条僵死的灰蛇,匍匐沉睡的屋舍之间。远处,黢黢的山峦际勾勒出锯齿状的剪,沉默地俯着这片被遗忘的土地。林穗走得很,几乎是跑,帆布包拍打着她的胯骨,面的书本和硬壳饼子硌得生疼。可她敢停,像停来,就被什么形的西拖回去,拖进那间低矮的土坯房,拖进那眼就能望到头的生。
村那棵歪脖子槐树出,她的脚步由主地慢了来。那棵树据说有年了,树干粗得要合抱,树皮皲裂如的脸。夏,村都爱聚树乘凉、扯闲篇;冬,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的空,像数只乞求的臂。
此刻,树蹲着个黢黢的,缩团,像块被遗忘那的石头。
林穗的猛地坠,沉到了冰窖底。她停住脚步,隔着几米的距离,和那个对峙着。风更了,卷起地的枯叶和沙土,打她的脸,生疼。
动了,缓缓站了起来。是而瘦的个轮廓,背有些驼,是常年弯腰干农活留的痕迹。即使隔着这么远,即使这么暗的光,林穗也能眼认出——是阿贵。
她的指死死抠进帆布包的背带,粗糙的布料摩擦着掌,带来丝尖锐的痛感。她深气,那气冷得像冰碴子,路扎进肺。然后,她迈脚步,是朝着他,而是绕过他,沿着那条往村的灰土路,继续往前走。脚步更,更急,像是身后有恶鬼追。
“穗儿。”
他喊她,嗓子哑得厉害,像被砂纸磨过,又像几没喝水。
林穗没应声,甚至没回头。她只是咬紧了牙关,把帆布包的带子攥得更紧,指甲几乎要嵌进。脚的路越来越,几次差点崴了脚,旧胶鞋的鞋底太薄,硌得脚生疼。可她能停,能停。
“穗儿!”阿贵追了来。他的脚步声很重,踩冻硬的土路,发出闷闷的咚咚声。他把扯住她的胳膊,那劲得惊,滚烫,带着常年干农活留的厚茧,粗糙得像砂纸,硌得她生疼。
林穗猛地挣,没挣。她终于转过身,昏暗的晨光,对红的、布满了血丝的眼睛。阿贵的脸朦胧的光显得格苍,嘴唇干裂,起了皮,巴冒出青的胡茬。他起来像是没睡,,也许几都没睡了。
“松。”她的声音比这凌晨的风还冷,冷得已都打了个寒颤。
阿贵松,反而抓得更紧,指几乎要掐进她的。他低着头,林穗能见他蓬蓬的头发顶和剧烈起伏的、薄的肩胛骨。他身那件打了补的旧棉袄,袖和肘部已经磨得发亮,棉絮从破处钻出来,风瑟瑟发。
“别去,穗儿,算我求你。”他声音带了哽咽,那哽咽堵喉咙,让他的声音扭曲变形,“那地方……那地方,骨头都吐。你听我的,咱就村,我……我以后肯定对你,我种地、我打工,我养你,我……”
“你养我?”林穗猛地甩他的,力气得已都往后踉跄了步,帆布包重重砸腿侧,面的书发出声闷响。她抬起头,眼睛像烧着两簇冰冷的火,那火苗暗跳跃,几乎要喷出来,“你拿什么养我?拿你家那间漏雨的土坯房?拿你爹欠了屁股的债?还是拿这满地爬出去的土坷垃?”
每个字都像淬了冰的刀子,从她嘴掷出来,扎阿贵脸。他的脸更了,得像地的霜。嘴唇哆嗦着,翕动了几,却发出何声音。那红的眼睛,有什么西迅速黯淡去,碎裂来。
他身后,是那道低矮的、用碎石和泥垒起来的院墙。那是林穗家的院墙。墙糊着的报纸早已被风雨撕烂,条条垂来,风力地飘荡。他就对着这道墙,跪了。林穗这才注意到,他膝盖处的裤子,沾满了泥土,湿漉漉的,晨光显出深的印子。
“城干净,都是的。”阿贵固执地重复着,像是背诵某种经文,又像是溺水的抓住后根稻草,“他们欺负你,骗你,你个娃子……你知道隔壁村的春霞?她出去打工,回来的候……回来的候都变啥样了?还有镇头的秀英姐,去了南方,年了,音信,她娘的眼睛都哭瞎了……”
“那是她们!”林穗打断他,胸剧烈起伏,每次呼都带着汽,喷两之间冰冷的空气,“我是春霞,也是秀英!我林穗跟他们样!我受够了,阿贵,我的受够了!我受够了每亮就起来挑水,受够了走几山路去学,受够了冬脚长满冻疮,夏被蚊虫咬得浑身是包!我受够了着我妈每愁眉苦脸,算计着锅那点米还能撑几!我受够了这破地方,受够了这穷子!我宁可被城欺负死,骗死,我也要像我妈那样,辈子困这院,着样的山,走着样的路,后埋后山,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有!”
她几乎是吼出来的,声音寂静的凌晨出很远,撞远处的山壁,又荡回来,变空洞的回响。有早起的家亮起了昏的灯,狗被惊动了,零零星星地吠起来。
阿贵像是被她的吼声震住了,呆呆地着她,那红的眼睛,后点光也熄灭了,只剩死灰样的绝望。他张了张嘴,喉咙发出嗬嗬的声响,像是破风箱拉扯。
林穗再他。她怕已再眼,再眼他眼那种破碎的、毫生气的光,她就软,就崩溃,就丢肩这个轻飘飘却重如钧的帆布包,就跟着他回去,回到那个漏雨的土坯房,回到那条眼就能望到头的土路。
她猛地转身,朝着那条灰土路的方向,跑了起来。是走,是跑。用尽了身的力气,像是要逃离什么洪水猛兽。帆布包重重拍打着她的胯骨,生疼。脚那旧胶鞋跟趟,几次踩进土坑,脚踝扭得生疼,可她敢停,也能停。冷风灌进喉咙,像刀子样割着,肺火辣辣地疼,可她只是拼命地跑,跑。
身后来“噗”声闷响。
是膝盖重重砸冻硬的土地的声音。那么沉,那么闷,像是直接砸了林穗的,让她狂奔的脚步猛地个趔趄。
然后是阿贵嘶哑的、变了调的哭喊。那声音像发出来的,更像是受伤的兽,绝境发出的后哀嚎,凄厉,绝望,能撕破的耳膜,能刺穿这沉沉的。
“穗儿——!!!”
声音拉得很长,尾音颤着,破碎风。
“我等你!我就这儿等你!你混就回来!我远这儿——!!远——!!!”
“穗儿——你听见没有——!!我等你——!!”
声又声,像钝刀子,刀刀割林穗的背。眼泪终于冲破了堤坝,汹涌而出,滚烫的液冲出眼眶的瞬间就被冷风吹得冰凉,变冰冷的盐渍,刀割似的贴脸颊。她敢回头,能回头。她只是跑,拼命地跑,把那嚎哭声,把那跪冰冷土地的身,把那道低矮的土墙,把那座沉睡的村庄,把她的过去,把她八年的生,统统甩身后,甩进那边际的、浓得化的暗。
直到那嚎哭声越来越远,渐渐被风声吞没,被她已粗重的喘息和狂的跳声覆盖,直到再也听见。
她终于跑动了,弯腰,撑住膝盖,地喘着气,喉咙是血腥味。冰冷的空气像冰碴子样灌进肺,刺得生疼。她直起身,回头望去。
村庄已经见了,被起伏的土坡和吞没。只有边,泛起了淡、朦胧的鱼肚。那点亮光弱得可怜,却固执地撕的角,预示着黎明终究来。
她站这荒凉的路边,前路是望到头的灰土路,蜿蜒着伸向未知的远方;身后是她生活了八年、如今已消失暗的故乡。寒风呼啸着穿过旷,卷起她的头发和衣角,薄的棉袄根本抵挡住这透骨的寒意,她控住地瑟瑟发,牙齿磕碰,发出咯咯的轻响。
可是那团火,那团从到录取知书那就点燃的、弱却肯熄灭的火,还烧着。烧得她胸发烫,烧得她眼睛发亮。
她抬起,用冻得红、几乎失去知觉的指,抹去脸的泪痕。然后,她转过身,背对着来路,面向着边那光,再次迈了脚步。
这次,走得很慢,却很稳。步步,踩冰冷坚硬的土地,发出沉闷的、坚定的声响。
镇的长途汽站,与其说是站,如说是片坑洼的空地搭了个漏雨的棚子。刚蒙蒙亮,这却已经聚集了。空气弥漫着劣质烟草、汗酸、尿,还有知道什么西馊掉的混合气味,刺鼻得让作呕。几个扛着编织袋、衣衫褴褛的民工蜷缩墙角打盹,脸写满了疲惫和麻木。几辆破旧的巴像奄奄息的兽趴那,身糊满了泥浆,油漆斑驳脱落,窗玻璃灰蒙蒙的,有的还裂着蛛般的纹路。
林穗挤群,紧紧抱着她的帆布包,像抱着后的浮木。她的旧胶鞋沾满了路的土,裤脚也被露水打湿了,贴冰冷的皮肤。寒冷和饥饿像两条毒蛇,缠绕着她。她找了个稍避风的角落蹲,从帆布包摸出母亲用油纸包的饼子。饼子已经冷了,硬邦邦的,但她地、珍惜地咬着,就着军用水壶冰凉的冷水咽去。每,都像是吞点薄的力气和决。
“去省城的!去省城的了!”个叼着烟圈、满脸横的司机扯着嗓子喊道,唾沫星子寒冷的空气变雾。
群动起来,争先恐后地往那辆起来破旧的巴挤。林穗被裹挟间,身由已地往前挪。有踩了她的脚,有用的编织袋撞了她的腰,她闷哼声,死死护住怀的帆布包,咬牙挤了去。
比面更糟。座位肮脏堪,露出面发的绵。过道塞满了行李和蹲坐的,几乎处脚。空气浑浊得几乎凝滞,混合着、食物、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腐败气味。林穗缩靠窗的个硬座,把帆布包紧紧抱胸前,脸贴着冰冷肮脏、凝着厚厚垢的窗玻璃。玻璃面,是飞倒退的、悉的景象:光秃秃的土坡,零星散落的低矮房屋,牵着慢悠悠走过的农,寒风瑟瑟发的枯树……这些了八年的风景,此刻正以种缓慢而决绝的姿态,向后退去,越来越模糊,越来越,后缩地交界处道起眼的、灰的褶皱。
子颠簸得厉害,像醉汉样坑洼的土路摇晃。林穗的胃阵江倒,她死死咬住嘴唇,把那股恶感压去。能吐,吐了就什么都没得了。她闭眼睛,努力去想知书那八个字,去想那些书到的、关于城市的模糊描述:楼厦,水龙,灯火明,机遍地……
知过了多,子发出声的、类似叹息的刹声,停了。省城汽站到了。
这比镇那个站嘈杂倍。声鼎沸,喇叭轰鸣,各种音的卖声、争吵声、哭喊声混作团。楼多了起来,虽然起来灰扑扑的,但确实比村的土坯房多了。林穗茫然地被流推着往前走,像片掉进流的落叶。她紧紧攥着帆布包,是冷汗,眼睛警惕地扫着周围陌生的面孔、陌生的建筑、陌生的切。
按照录取知书背面印的简陋交指南,她要去火站,坐往的火。问了几个,跌跌撞撞,终于找到了公交站。又阵令晕头转向的拥挤和推搡后,她挤了辆塞得像沙鱼罐头似的公交。子走走停停,每次刹和启动都让她胃。窗掠过更多更的楼房,更多的商店,更多的,更多的。切都那么嘈杂,那么匆忙,那么……冰冷。
火站像个的、喧闹的蜂巢。耸的穹顶,是压压的头。空气浊堪,混杂着汗味、泡面味、灰尘味,还有某种焦躁安的气息。的列刻表处闪烁,红红绿绿的字停滚动。拖着包包行李的们行匆匆,脸写着疲惫、焦急、期待或茫然。广播声用毫感的语调断播报着次信息,夹杂着刺耳的流杂音。
林穗仰起头,着那些闪烁的、她几乎懂的字符,着那些拖着比她整个还的行李、步履沉重的们,次感到种的、几乎将她吞没的惶恐。这和村,和镇,甚至和省城的汽站,都样。这的切都太了,太了,太嘈杂了,太……了。她像个误入的,渺,助,格格入。
她攥紧了的帆布包,指甲深深陷进掌,用那点尖锐的疼痛来对抗底蔓延来的恐惧。她找到了售票窗,那队伍长得见头。她默默排到队尾,低头着已沾满尘土的鞋尖。周围是各种各样的声音,抱怨,争吵,孩子的哭闹,打话的声喊……汇片令头晕目眩的噪音洋。
排了知道多,腿都站麻了,终于轮到她。隔着厚厚的、迹斑斑的玻璃,她递录取知书和那叠被母亲绢包裹得严严实实的,翼翼地说:“张去的硬座,学生票。”
售票员是个涂着鲜艳红的年,眼皮都没抬,指油腻的键盘噼啪啦敲打着。“证明。”她耐烦地吐出两个字。
林穗赶紧又把录取知书往推了推。
瞥了眼,从鼻子哼了声,撕张票,连同找回的零,起从窗面那个凹槽扔了出来。硬币属槽叮当作响,滚得到处都是。
林穗慌忙蹲身去捡,脸涨得红。周围来几道或同或漠然或略带嘲讽的目光。她把散落的硬币枚枚捡起来,擦干净,和票起,仔细地进贴身的袋,按了按,确认了,才松了气。
离还有几个。她敢走,就候厅个相对的角落找了个空地,把帆布包抱怀,靠着冰冷的墙壁坐。饥饿感更烈了,但她舍得再饼子,那是她接来知道多个唯的干粮。她只能抿着水壶所剩多的凉水,闭眼睛,试图忽略周围嘈杂的声和肚子咕噜噜的抗议。
间秒地过去,候厅的光渐渐暗淡,又亮起惨的光灯。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。有穿着面、拖着致行李箱的男,有背着蛇皮袋、满脸风霜的民工,有抱着孩子、满脸愁苦的妇,也有像她样,拿着录取知书、眼混杂着兴奋和安的年轻面孔。
终于,广播响起了她等待已的次信息。她像弹簧样跳起来,背帆布包,随着汹涌的流,挤向检票。检票,进站,到月台。
然后,她见了它。
绿皮火。像条沉默的、墨绿的钢铁兽,静静地卧铁轨。身很长,长得望到头。窗透出昏的光,映出面晃动的。厢壁沾满了灰尘和渍,有些地方油漆剥落,露出底暗红的铁锈。它起来陈旧,疲惫,甚至有些肮脏,可是,它就要带着她,离这,去往那个只梦和书出过的、的地方。
林穗的,那刻,狂跳起来。是恐惧,而是种近乎窒息的动。她随着流,被推挤着,涌向其节厢的门。列员站门,声吆喝着,催促着们。她几乎是被流卷着,挤了。
厢的景象让她瞬间窒息。,到处都是。座位挤得满满当当,过道也站满了,蹲满了,甚至座位底都塞着蜷缩的身。空气浊得令作呕,混合着气味、泡面味、汗味、脚臭味,还有某种说出的酸腐气息。灯光昏暗,照着张张疲惫、麻木或焦躁的脸。
她捏着那张的、印着座位号的票,像握着根救命稻草,拥挤堪的过道艰难地挪动,断地说着“借过,借过”,声音细若蚊蚋。容易找到已的座位,是靠窗的个位置,但座位已经坐了个抱着孩子的胖婶,正把湿漉漉的尿布摊桌板晾着。
林穗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可着婶那耐烦的和周围拥挤堪的境,她默默地把话咽了回去。她把帆布包紧紧抱胸前,侧着身子,挤进了座位和前面靠背之间那点点狭窄的缝隙,勉站稳。子动了,发出沉闷的、有节奏的“哐当、哐当”声,缓缓驶离了站台。
窗的景始移动。先是站台迅速后退的灯光和群,然后是城市边缘杂章的建筑,接着是越来越稀疏的灯火,后,是边际的、沉入暗的原。只有铁轨两侧偶尔掠过的、孤零零的路灯,窗飞流转的光带。
厢,有始声聊,有打牌,有哄孩子,有干脆靠行李打起了呼噜。各种声音交织起,混合着列行驶的噪音,形种停歇的背景音。林穗缩那个狭窄的缝隙,腿很就麻了,腰也酸得厉害。但她敢动,也动了。她只是紧紧抱着她的帆布包,脸贴着冰冷肮脏的窗玻璃,眼睛眨眨地着面飞驰而过的暗。
那暗浓稠如墨,什么也见。只有窗玻璃,模糊地映出她已苍憔悴的脸,和厢晃动的。她着玻璃那个陌生的、模糊的倒,忽然感到阵的、依靠的茫然。
这就是厉害吗?这就是去往新界的路吗?为什么没有想象的雀跃和动,只有沉甸甸的、冰冷的疲惫,和丝丝越来越清晰的恐惧?
阿贵嘶哑的哭喊声,毫预兆地又耳边响起:“穗儿——!!我等你——!!”
她猛地闭眼睛,把额头抵冰冷的玻璃。玻璃的凉意透过皮肤,直刺进脑子,让她打了个寒噤。,能想。能回头。弓没有回头箭。这是她已选的路,跪着,也要走去。
列“哐当、哐当”,知疲倦地行驶边的。穿过原,跨过河流,钻过隧道。厢的灯熄灭了,只留几盏昏的灯。多数倒西歪地睡着了,发出各种鼾声和梦呓。空气变得更加浑浊闷热。林穗又累又困,腿脚早已麻木得失去知觉,可她敢睡,也睡着。怀这个硬壳笔记本,和面那张薄薄的纸,是她部的身家命。她须清醒地守着。
间失去了意义,只有列调的轰鸣和窗恒的暗。偶尔经过某个站,到几点寥落的灯火,飞地向后掠去,像被遗弃旷的、孤独的眼睛。
知过了多,边终于泛起了丝灰。那先是淡淡的,像蒙了层灰的宣纸,然后慢慢浸润来,染点淡的、几乎见的青。暗始退却,窗,田、村庄、树木的轮廓,点点从混沌浮出来,像是褪的水墨画。
林穗直睁着眼睛,着这光点点亮起。当缕正的晨光,穿过浊的窗玻璃,落她脸,她感到种近乎虚脱的疲惫,和种奇异的静。
,终于亮了。
列个站停靠,又是阵拥挤和混。有,更多的。林穗趁着这个机,活动了几乎僵硬的腿脚,从帆布包拿出水壶,抿了早已冰凉的水。干粮只剩后半个饼子了,她掰了块,含嘴慢慢化着,舍得完。
窗的景,知觉,已经彻底变了模样。再是调的、望际的田和土坡。始出了片片整齐的农田,的塑料棚阳光反着刺眼的光。房屋越来越密集,样式也新奇起来,再是低矮的土坯房,而是两层的楼,贴着的瓷砖。接着,是片的、样式统的厂房,的烟囱冒着烟。再然后,房屋的密度陡然增加,变了连绵的、低矮的楼房,街道纵横交错,汽像甲虫样道路爬行。
城市。个又个城市,窗掠过。它们起来同异,灰蒙蒙的空,是灰蒙蒙的楼房,灰蒙蒙的街道。但林穗知道,这都是她的目的地。她的,随着列越来越的速度,也越跳越,混合着期待和安,胸腔擂鼓。
,当列广播终于响起那个她等待已的名字,林穗觉得已的脏几乎要跳出喉咙。
“旅客朋友们,列即将到达本次行程的终点站——站,请您收拾行李物品,准备……”
厢瞬间动起来。们纷纷起身,拖拽行李,呼喊同伴,孩哭闹。林穗也站了起来,腿脚因为坐和长间保持个姿势而麻木刺痛,她踉跄了,扶住前面的座椅靠背才站稳。她背帆布包,那原本轻飘飘的包,此刻却觉得有斤重。
列缓缓滑入站台,速度越来越慢,后,“哐当”声,彻底停稳。门打,混杂着各种气味的热浪和的声浪,瞬间扑面而来,将林穗吞没。
她被流裹挟着,身由已地挪厢,踏了月台。
瞬间,她以为已失聪了。
那是种难以形容的、庞而混沌的噪音。火的汽笛声,广播断重复的声,鼎沸的声,推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,拉客的吆喝声,远处城市隐约来的流声……所有这些声音混起,形种持续断的、震耳欲聋的轰鸣,像头见的兽耳边咆哮。
空气是粘腻的,潮湿的,带着种陌生的、混合着煤烟、汽油、灰尘和某种说清道明的料的味道,热烘烘地包裹来,让她几乎喘过气。
她抬起头。
然后,她见了空。
,那几乎能算空。那是片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、灰蒙蒙的穹顶。所及,是数耸入的、怪物样的建筑。它们挤挤挨挨,摩肩接踵,用冰冷的玻璃和钢铁的身躯,霸占了几乎所有的空间。阳光被它们切割、反,变道道刺眼而冰冷的光束,胡地来。只有从这些庞然物狭窄的缝隙,才能到片被染灰蓝的、那么净的。
这就是。
这就是她拼了命,抛弃切,也要抵达的地方。
她站原地,动弹得。像尾被突然抛岸的鱼,张着嘴,却呼到氧气。周围是汹涌的潮,们面表地、急匆匆地从她身边走过,撞得她倒西歪,却没有多她眼。她和她那个洗得发的帆布包,她脸茫然措的表,她身与这座城市格格入的土气,这片,渺得如同入的粒沙,瞬间就被吞没,了痕迹。
过了很,也许只有几钟,也许有个纪那么长,林穗才猛地进气。那气带着城市有的浑浊气味,呛得她咳嗽起来。她握紧了帆布包的背带,粗糙的布料摩擦着掌,带来丝悉的触感。然后,她迈脚步,像周围所有样,低着头,汇入了那停歇的、奔向面八方的流。
出处是更加广阔、更加嘈杂的厅。耸的穹顶,光滑得能照出的理石地面,的指示牌闪烁着颜的光。们拖着行李箱,行匆匆,奔向各个出,奔向出租排队点,奔向地铁入。切都那么井然有序,又那么冷漠疏离。
林穗茫然地跟着指示牌,走向出。动门打,更加喧嚣的声浪和炽热的阳光起涌来,让她眯起了眼睛。
站前广场,是的洋,的洋。数辆排着长龙,耐烦地鸣着喇叭。公交笨重地驶过,出租灵活地穿梭。楼厦的玻璃幕墙反着刺眼的光芒,幅的广告牌,妆容完的明星和模带着恒的笑,俯瞰着脚蝼蚁般的群。
她站广场边缘,炙热的阳光晒头顶,额头很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汗水顺着鬓角流来,痒痒的,她也顾擦。她只是仰着头,着那些耸入的建筑,着那些闪烁的霓虹灯(即使,有些灯也亮着),着那些穿着光鲜、步履匆匆的们,着那些她只和书本见过的景象。
这就是她未来要生活的地方。
这就是她梦想始的地方。
可是,为什么空落落的,没有想象的狂喜,只有种沉甸甸的、几乎要将她压垮的茫然,和丝深藏着的、连她已都敢去触碰的恐惧?
阿贵嘶哑的声音,又次,鬼魅般地底深处响起:
“城,你别去。”
她猛地甩了甩头,像是要把那个声音从脑驱赶出去。指甲深深陷进掌,疼痛让她清醒。
。她来了。她已经这了。
没有退路了。
她深气,那气充满了汽尾气的味道。然后,她挺直了因为长途跋和茫然措而有些佝偻的背,握紧了帆布包的带子,迈脚步,朝着广场,朝着那片钢筋水泥的森林,朝着那未知的、充满限可能也暗藏数凶险的未来,步步,走了过去。
薄的身,很就被淹没八月后炙热而喧嚣的潮与流,像滴水,汇入了。